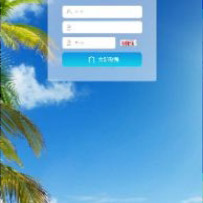广义上来说,艾滋病是世界范围的世纪绝症。由于其主要传染源是患者的分泌物和血液,所以,医务人员与患者的接触存在着相当的高危性。
2008年,我报名参加广东省第24批赴非洲赤道几内亚医疗队并入选。当时,女儿正读初三,眼看要考高中,丈夫反对我在这个时候出远门。妈妈和舅舅,以及从小习惯我下班不准时、节假日加班的女儿,却表示理解和支持。丈夫一看被“孤立”,也就改投赞成票,但提出一条硬性要求,那就是不要接触艾滋病患者。我也知道艾滋病的厉害,临走前专门向有关医学专家讨教防范措施,还准备了几十套防护面罩、高强度高韧性橡胶手套……
到了赤道几内亚,我才知道那里的人群发病率比统计数据要高得多,很难避开和这类病人接触。何况艾滋病患者也是人,谁也不能剥夺他们生存和治病的权利。我虽害怕,但还是告诉自己,要做好与艾滋病患者零距离接触的准备。
第一次接触是一天清晨,医院的电话把我召回产房:一位产妇胎头持续不降,胎儿宫内窘迫,情况紧急。
我赶回医院,只见产床上躺着的27岁产妇大喊大叫,丝毫不配合医生检查治疗。病历显示她生过三个小孩都是早产,腹中的孩子37周加3天,已是足月。我吩咐助手:马上剖腹产!但那位异国同行却把拉我到门口,掏出一张化验单——HIV(+),原来是艾滋病毒携带者。我猛地一惊,但此刻已别无选择,必须上!
刚打开病人腹腔,一股难闻的异味扑鼻而来,腹腔里肠壁和子宫表面的血管呈现异常扩张,我判断这个病人处于发病期,情况更加复杂了。偏偏这个时候电动吸引器出故障,没法吸出羊水,瞬间,伴随着胎儿大便以及掺和母体艾滋病毒的羊水四处流淌。医生的本能使我顾不上害怕,为了安全取出婴儿,个子不高的我不得不踮起脚尖,右手托着胎头,左手帮着助手压产妇子宫底,整个人几乎趴在手术台上,挨着产妇的身体,尽管隔着防护围兜,我的裤腿及双脚还是被羊水浸透了。幸好新生儿经过简单的抢救后发出了第一声啼哭,我悬着的心这才放下。
从手术室出来,我直奔办公室,来不及脱下手术衣就吐得昏天黑地!这时,会不会感染艾滋病毒的担心再次袭来。
中午回到宿舍,QQ上老公的头像在闪,我机械地打出早已设置好的快速回复:“很好,没有手术,也没有接诊过艾滋病人。”看着老公回给我一个笑脸,泪水顷刻间涌上眼眶。
过后经过检验,结果是阴性,我才稍稍放下心来。有了第一次与艾滋病人的零距离接触,我的胆子似乎变大了,我想,只要加强自身防范,是能够抵御艾滋病毒感染的。这之后,我多次给艾滋病患者看病治疗动手术,取得了好的效果,很多病人来到医院妇产科,专门找我诊治。每次门诊,我还没有上班,患者就在门外排起了长队。
还有一次,我给一个HIV阳性的患者做手术,她是来割除多发性子宫肌瘤的。一年前她怀孕5个月时不明原因流产,刮宫时发现多发性子宫肌瘤。尽管有医生告诉她,流产很可能是肌瘤引起的,也不排除她的HIV阳性,就有可能是流产的免疫因素,但对于她肌瘤是在当地唯一能查出来并通过手术治愈的疾病,所以,这个首次怀孕就流产的病人迫切要求尽快手术,她反复说:我只想要一个孩子……面对这位渴望当母亲的艾滋病毒携带者,我没有拒绝。
在赤道几内亚行医,常遭遇“意外”,如手术器械运转失灵、助手临时被抽去急诊室帮忙等。我唯有在当时的条件下,和两位没什么经验的助手,共同完成这台手术。幸好我们的队友麻醉师一如既往的给力,幸好手术中电刀一直能正常转动,幸好病人盆腔的粘连也不严重。我细心而又利索地操刀,一共挖出大大小小8个肌瘤,还给左侧输卵管伞端闭锁行造口术,术后又进行了一系列治疗。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零距离接触,为了我的病人能顺利怀孕和分娩,我必须尽医者职责。
在经历了无数次与艾滋病毒“零距离接触”却擦肩而过之后,我对“恐艾症”产生了强大的免疫力,并积累起丰富的“抗艾”经验。
回国两年多来,那段经历始终不能忘怀,我常牵挂非洲的艾滋病患者,祈祷他们平安健康。
栏目:人物故事